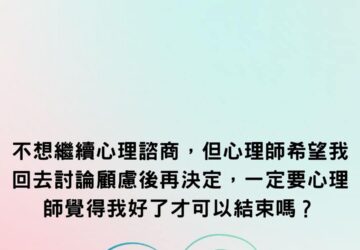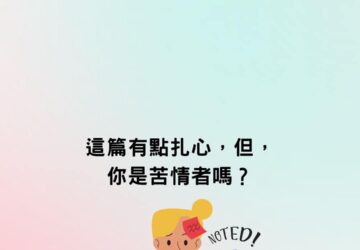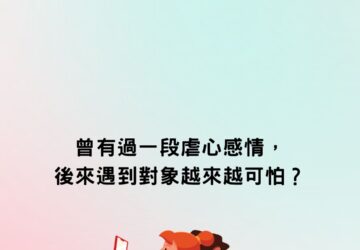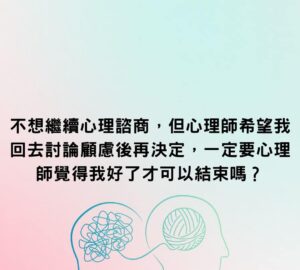作者:吳姵瑩Chloe Wu 諮商心理師
當時我高二,心理治療與心理醫師這些詞彙總讓我憧憬與好奇。
班上有個女孩經常請假,因為太少參與,自然邊緣化,即使來學校上課,也總是到其他班級找她的朋友,也不知道為什麼,我慢慢成為女孩的閨蜜,她開始跟我說了很多事,包括她去看心理醫師的事。
「他好帥好年輕,而且也他單身,我都準備好要嫁給他了。」
我聽來聽去,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她不斷重複對他外表與溫柔特質的讚美,小時候看少女漫畫長大的我,把他的心理醫生想成漫畫中的花美男,好奇怎麼會有人如此帥、如此聰明又如此溫柔,這般完美還是個我最嚮往的職業,我也跟著冒了一堆粉紅泡泡。
女孩曾經有一段時間病情嚴重住院,沒辦法來上課,女孩告訴我他的醫生對他有多照顧,醫生也給了他手機,因此她有辦法傳簡訊給他。我更加納悶了,雖然眼前的女孩是我同學,但醫生這麼照顧病人我到頭一次聽說,當時我的母親常跑醫院,也沒見半個醫生有這般照顧。
在某一個週末,女孩找我一起去唸書,她告訴我醫生也會去,我實在不可置信,在我青少女的視框裡,在滿是「要考上醫科」的校園氛圍裡,那種感覺就像中了頭獎吧!女孩告訴我他約醫生教他數學物理,知道我理科怎麼讀都讀不好,我也樂得跟她一起見見這個神秘嘉賓。
我跟女孩有點侷促不安的坐在麥當勞二樓,眼光一直若有似無的飄向樓梯口,我搜尋著我想像的花美男,女孩則是撥頭髮還拿出補妝的鏡子,直到樓梯口傳來三步併作兩步的腳步聲。
那不是花美男,我對於接下來可能只有半小時的學習,變得極度意興闌珊。
沒有濃密的頭髮,沒有細長的鼻子,沒有迷人的電眼,沒有纖瘦的身形,沒有平滑的膚質,沒有高雅的品味,倒是有點吊兒郎當的氣息,以及小女生不會再多看一眼的模樣。
你說我高中時期就極度外貿協會,我是不會辯解的,只是我對女孩在他面前無時無刻的溫柔乖巧、迷戀順從感到極度困惑,我也對於一個執業醫師願意免費家教這件事感到不可思議。
女孩眼睛裡的迷戀與醫師眼神裡細微得意的光芒,在那週末的午後相互映照著。
也許醫生為了鼓勵他,因此對他說:等你出院我帶你去喝咖啡。
也許醫生為了幫助他,因此願意在下班時間,還抽空到麥當勞為她惡補缺課的課業。
也許醫生疏忽了,在治療中的女孩已經投放過多依戀和移情,卻沒有適時地停止。
也許醫生也需要這份迷戀與依賴,來成就心中那份,也許我不論多少歲,都被小女孩愛慕。
究竟醫生拒絕不了的,是女孩?還是心中的情慾?
女孩的故事我的印象只到這裡了,因為後來女孩也沒有繼續跟我同班,我最後的印象只停留在班導很緊張得找到我,問我知道些什麼,也許基於保護,也許擔心謠言四起,但終究我與女孩斷了聯繫,她徘徊在休學與復學之間。
至於青少女的我與治療師的經驗,因為對催眠太感興趣,找到可以免費做心理治療與催眠的機構,而我遇上非常好的治療師,只記得那是在新崛江商圈附近某某書院,開放給大眾唸書的地方,雄女的孩子想在外面唸書時就會去那裡,因此我遇到我的治療師,被我纏著做了幾次前世回朔,以及療癒性超高的童年創傷的治療,而最終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,是我拿著高中時候的相本跟他說我的人際困擾時,他仔細看著相本後告訴我:「你跟身邊的人都笑得很開心,我實在很難看出你人緣不好。」
他說的,是一張我們雄中雄女大露營的照片,因為他這句話,我重新改觀了我對人際與人緣的看法。
當然,我願意改觀,是因為前面好幾次他細緻又穩定地接住我的情緒,而在那一刻他的話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撼動,我與他的治療關係,始終只維持在治療室中,最多也只有在我們結束關係後,我到書院讀書時,從門縫跟他打招呼,而他總是淡定地點頭回應我。
我的故事很沒戲唱也缺乏張力,卻有著顯著影響的力道。
治療改變的發生,基本上最關鍵的還是指向治療關係,這也是心理師謹守倫理防線中最重要的一環,不與案主有治療情境外的互動,對我而言是保護我的精力與時間,因此我向來懶得在工作情境之外回答私人問題,對案主而言也是保護他們,避免對諮商師有過多的期待,避免關係進展到私人關係,因為,真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就一腳跨過去了。
女孩小鹿般無助的雙眼,在治療師的引導下綻放喜悅的笑容,治療師的英雄情結或拯救者情節一旦被喚醒,可能會希望她可以藉由自己的力量讓案主「更幸福」。
女孩寂寞孤單缺乏被愛的感受,在治療師的陪伴下覺得自己被理解與接納,治療師剛好也需要去愛與愛人,治療關係在一方專業一方脆弱中的權力不對等,關係的走向很容易由治療師一手操控。
治療師的專業,不會只是治療方法、知識與取向,還包括個人身心靈的修煉,包括身口意的覺察,也就是行動、語言與意念在自身是如何流轉。
一個可以嗅到自己也有渴望救贖他人、渴望被需要、渴望被崇拜的治療師,就要能立即踩剎車,因為採不住的下一步就是滿滿的傷害,而最終強烈滿足的卻是治療師個人,因為案主在治療情境中是某種程度渴望治療師的「愛」,而容易失去拒絕的話語權,總是到了關係極度退潮後,案主才可能意識到自己被傷害。
一個治療師,是樂意案主經過治療後,開心快樂的宣示要離開治療,而非嘗試建構持續性的依賴,讓案主一直需要這段關係。一個治療師更要在感受到案主對自己的情愫,或自己對案主的情愫發生或即將發生時,能夠即時轉介或討論治療關係,避免情愫蔓延到不可收拾,而這些治療界限的拿捏,說穿了是治療師個人意識的延伸,你自我的樣子,就會是關係界限的樣子。
註:台灣沒有心理醫生,只有精神科醫生/身心科醫生,青少女時期認為的心理醫生其實就是精神科醫生,有的精神科醫生有特別接受心理治療不同學派的訓練,因此有能力做心理治療,但有的精神科醫生並不崇尚談話性治療,因此也有區別。
心理師並非心理醫師,領有衛福部心理師執照,無法開藥與給予診斷,但多數擅長不同取向的談話性治療,風格與人性觀也因此極大差異,但通常不建議過度「心理雪拼」,換過一個又一個心理師或機構,有機會再與大家分享原因。
陪伴你成長:【關係界限】建立自尊與原則的人生

▌喜歡我的文章,歡迎訂閱▌
[mc4wp_form id =“3311”]